- 依內容分級制度,未登入僅能顯示普遍級內容,登入後即可觀看全站內容。
- 馬上登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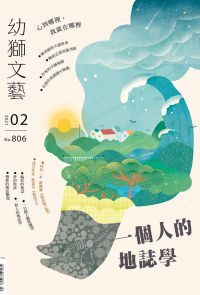
關注
關注作者、出版社、系列,新刊上架可獲得通知!
 放大
放大
內容簡介
幼獅文藝2021年02月號806期
【一個人的地誌學】
你用什麼記錄每一程生命行旅和留佇的地點?你有自己獨家版本與主題的生活、工作、創作地圖,且以手寫心的,真的動筆描繪出來?
那會是什麼?不只是動線、空間感或記號。
是否,會是一些聲響、氣味、畫面;是一棵樹,一道流水的路徑;或一些笑臉,幾段不介意缺損前後文的記述;第一口咬嚼的滋味,某件小物枕在手中、難以言說的沉甸感?
或是,傷碎的心,連自己都幾乎遺忘的祕密,凝視良久的禽鳥猛然振翅飛起……
「地誌學」原作為「對某一地方的描繪」的行動與技藝,到今日,其原屬於空間、時間、人交互作用、創發的,語彙、思考和呈顯方式,也有了相當超展開的想像、詮釋、孳衍、應用,更是記憶、專業、情意的載錄方式,與溝通體系一種。
一個人,能去到多遠,多深,感受多幽微?地誌既是觀察、紀錄的方法,是孤獨的憑證,也是相遇的憑證。
■傾身細語
海圖/張卉君
恭喜迷失/劉崇鳳
■在路上
現在就出發!!/編輯部
■有圖可證
我來,也畫下來!/劉克襄
■與子偕遊
督旮薾的散步課/吳俞萱
■前往歷史
你以為歷史會在那裡等你但沒有/朱和之
■MOOK編者的行進
我的編輯地誌學/董淨瑋
■夢的地誌
據說這就是永恒/周曼農
■連結熟悉與陌異
陳柏言談《溫州街上有什麼?》/許楚君<
你用什麼記錄每一程生命行旅和留佇的地點?你有自己獨家版本與主題的生活、工作、創作地圖,且以手寫心的,真的動筆描繪出來?
那會是什麼?不只是動線、空間感或記號。
是否,會是一些聲響、氣味、畫面;是一棵樹,一道流水的路徑;或一些笑臉,幾段不介意缺損前後文的記述;第一口咬嚼的滋味,某件小物枕在手中、難以言說的沉甸感?
或是,傷碎的心,連自己都幾乎遺忘的祕密,凝視良久的禽鳥猛然振翅飛起……
「地誌學」原作為「對某一地方的描繪」的行動與技藝,到今日,其原屬於空間、時間、人交互作用、創發的,語彙、思考和呈顯方式,也有了相當超展開的想像、詮釋、孳衍、應用,更是記憶、專業、情意的載錄方式,與溝通體系一種。
一個人,能去到多遠,多深,感受多幽微?地誌既是觀察、紀錄的方法,是孤獨的憑證,也是相遇的憑證。
■傾身細語
海圖/張卉君
恭喜迷失/劉崇鳳
■在路上
現在就出發!!/編輯部
■有圖可證
我來,也畫下來!/劉克襄
■與子偕遊
督旮薾的散步課/吳俞萱
■前往歷史
你以為歷史會在那裡等你但沒有/朱和之
■MOOK編者的行進
我的編輯地誌學/董淨瑋
■夢的地誌
據說這就是永恒/周曼農
■連結熟悉與陌異
陳柏言談《溫州街上有什麼?》/許楚君<
作者簡介
幼獅文藝編輯群
(另一種)線上與線外世界 文/丁名慶
請先取出一張白紙(回收紙或廣告單皆可),或攤開筆記本空白頁。
畫一條線。
在線的一端寫下此刻所在空間,或時間、狀態。
另一端,寫下正要前往的空間,或時間、狀態,某事的階段性結果;記錄抵達方式、路線,沿途五感邂逅的人事物,以及心情──或簡化,或窮其細節地將之寫下,畫下(別管像不像了)。
在線上設定節點,代表每個必須逗留之地;處理某事、與某些人同在。有可能拉出支線──這訴諸機遇與個性──良心建議,節點與支線愈少愈好。若不可少,就設法增加可運用/耗費的時間總量。
這或許就是最素樸意思、日後重省才會意識其價值的「地誌」,或「前創作」了。
更多點玩心,就像個孩子那樣,把櫃上公仔、家人照片依照某種不必向誰說明(因而時光積澱,就成了祕密,或者遺忘)的邏輯,兵棋推演或者玩偶邀宴般,布列於地上桌上床上,使這些物件間形成一些關係、距離的親密或張力,邊界與詮釋曖昧的故事場景。瞧,是不是也像個等待解說的展覽空間呢?
我覺得,這也滿像每次雜誌在規劃專輯之初,必然會有的「還不知道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內容」無窮可能性時期,僅能一步步朝外忐忑跨出,調校,轉向,並落實那個頗堪玩味的說法:「在有限空間(尤其是紙本)中,把空間做出來。」這樣說來,一本雜誌,竟也有幾分像是既安靜也熱烈地刻寫著自身時空間經歷地誌的一個人了。
請先取出一張白紙(回收紙或廣告單皆可),或攤開筆記本空白頁。
畫一條線。
在線的一端寫下此刻所在空間,或時間、狀態。
另一端,寫下正要前往的空間,或時間、狀態,某事的階段性結果;記錄抵達方式、路線,沿途五感邂逅的人事物,以及心情──或簡化,或窮其細節地將之寫下,畫下(別管像不像了)。
在線上設定節點,代表每個必須逗留之地;處理某事、與某些人同在。有可能拉出支線──這訴諸機遇與個性──良心建議,節點與支線愈少愈好。若不可少,就設法增加可運用/耗費的時間總量。
這或許就是最素樸意思、日後重省才會意識其價值的「地誌」,或「前創作」了。
更多點玩心,就像個孩子那樣,把櫃上公仔、家人照片依照某種不必向誰說明(因而時光積澱,就成了祕密,或者遺忘)的邏輯,兵棋推演或者玩偶邀宴般,布列於地上桌上床上,使這些物件間形成一些關係、距離的親密或張力,邊界與詮釋曖昧的故事場景。瞧,是不是也像個等待解說的展覽空間呢?
我覺得,這也滿像每次雜誌在規劃專輯之初,必然會有的「還不知道會發展出什麼樣的內容」無窮可能性時期,僅能一步步朝外忐忑跨出,調校,轉向,並落實那個頗堪玩味的說法:「在有限空間(尤其是紙本)中,把空間做出來。」這樣說來,一本雜誌,竟也有幾分像是既安靜也熱烈地刻寫著自身時空間經歷地誌的一個人了。
 「幼獅文藝」系列
「幼獅文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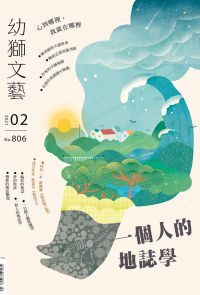
全系列作共96冊
相關推薦書刊
買此商品的人也買了...
購買前的注意事項
- 本書城的商品為電子書及電子雜誌,並非紙本書。讀者可透過電腦裝置網頁瀏覽,或使用 iPhone、iPad、Android 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閱讀。
- 如有下載閱讀需求,為避免裝置版本無法適用,建議於購書前,先確認您的裝置可下載BOOK☆WALKER的APP,並可先下載免費電子書,確認可順利使用後再行購書。
- 由於數位智慧財產權之特性,所販售之電子書刊經購買後,除內容有瑕疵或錯誤者外,不得要求退貨及退款。如有特殊情形,請洽敝公司客服人員,我們將盡速為您處理。
現在完成手機驗證,還可以領取一本免費電子書!




















